
他的名字很多人都没有听过,但是在浮躁喧嚣的当今社会,他以自己的奉献和坚守告诉了我们,什么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“流量”和责任担当。
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:荠麦青青
洞烛幽微,发掘名人世界的人性之光。
2017年9月25日,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、植物学家钟扬教授,在赴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,因车祸遇难。
曾经,这个在多少人眼里陌生的名字,在他英年早逝后,才得以广为人知。

钟扬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。生前,他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深夜
一名网友留言:很抱歉,以这样一种形式认识您。
太宰治在他的《人间失格》里有句话: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。”在虚无主义者眼里,一世为人,是一件“失格”的事情,抱歉“生”的困惑和死的谜题。
生而为人,我们抱歉什么呢?抱歉尚未兑现的诺言,抱歉一些错失的美好,甚至,包括一场迟到的了解......
生前,作为“国宝级”的科学家,钟扬援藏16年,采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,也在无数人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;去世后,他的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高标。

钟扬和学生们一起在采样的路上
· 01 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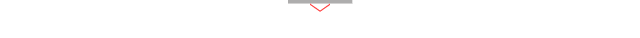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,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,从湖北黄冈中学考入中科大第三期少年班,学习无线电专业。
5年后,他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,专业不对口。
在场的植物专家故意开他的玩笑:这是什么?那是什么?
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下,钟扬开始埋头钻研,他拿着植物检索表一种一种地对照着认识。一年之后,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植物名称,全是拉丁语,“比受过正规分类学教育的人还正规”。

“板凳一坐十年冷”,从实习员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到升为副所长,钟扬在武汉整整工作了15年。
别人花15年,或许是为了仕途、头衔,但他却从蛮荒之地开垦出属于自己的“绿洲”。
十几年的经历,足够沧海桑田,但他对研究的执著始终如一。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架“打桩机”,穷极所有的热情与精力,向着植物学领域的纵深方向,一路挺进。
2000年,钟扬任放弃了摆在眼前的“副所长”职务,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授、博导。

他“跳槽”到复旦大学,实际上是希望从科学家,转型成为既搞科研又从事教学的大学教授。
三尺讲台,在他看来,可以是生命中的另一个“道场”。
2001年,钟扬再次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:主动请缨,只身踏上地球“第三极”——西藏,申请成为了援藏专家。
他入藏的愿望清单里,有一项重要的使命——采种子。

钟扬在赴西藏阿里途中
为什么要采种子?
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等原因,世界上75%的植物品种已消失了。
科学家们为了保护种子,在全球各地建造了大大小小的种子库,最为著名的就有挪威的斯瓦尔巴特种子库,被称为“末日种子库”。

著名的斯瓦尔巴特种子库
钟扬的课题组同事——南蓬教授——就提到:“在屠呦呦的青蒿素之前,还有一个治疗疟疾非常重要的药物——奎宁。它是从金鸡纳树中提取出来的。金鸡纳树原来分布在南美的秘鲁,被视为秘鲁国宝。可是这个国宝的种子被种子猎人盗取以后,栽种到了印度尼西亚。从此,印度尼西亚成为奎宁的出口大国。”

金鸡纳树
所以,毫不夸张地说,植物的种子和一个国家的石油资源一样重要:“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,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众苍生!”
然而现实情况如钟扬教授所说:非常糟糕的是,在了解和知道它(种子)能否被利用之前,它就已经没有了。
为了在种子消失之前了解和利用它们,钟扬教授选择了西藏,原因无他,因为青藏高原是生植物分布非常多样性的地区。
他说:“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,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,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。”
世人只道植物学家“走遍千山万水,撷取大自然精华”,却不知背后的颠踬艰辛不足为外人道。

钟扬和学生在可可西里
· 02 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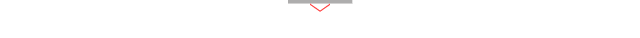
从2001年起,钟扬教授在西藏探索了整整16年。
在这16年的野外考察途中,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九曲回环的山路,掉下悬崖,訇然不见;没有水,就不洗脸,经常蓬头垢面;没有旅店,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;大雨、冰雹从天而降,就躲在山窝子里;还有几乎所有类型,甚至致命的高原反应……这些,钟扬一一历遍。
那时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——钟大胆。
但这个世上,哪有真正不怕死的人?不过是当热爱战胜了恐惧,他才成为了那个涉险“越境”,一往无前的勇士。
餐风饮露,胼手胝足,翻山越岭,九死一生,这是他在西藏最真实的写照。

野外考察采集植物
为了能多带一些装备和种子,钟扬就把食物简单化,他带着整个团队在西藏采样,“七天在只吃饼干、火腿肠、榨菜中度过,没有吃过一顿热饭”。
长期科考回来的钟扬,经常口腔溃疡,唇焦发枯,胡子拉碴,俨然“野人”。
他的挚友回忆他时不禁感慨万端:“那么多的艰苦,那么多的危险,也只有他,说起这些能云淡风轻,也只有他,扎根进去,就毫不犹豫,绝不回头。”

钟扬(右二)与西藏大学师生在西藏采集种子。这是他们在户外吃午饭。图片来源:新华社
钟扬生前最喜欢一首藏族民歌: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,出没于雕梁画栋;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,在高山砾石间绽放。
在十几年的时间里,他考察的脚步从未停下,走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,收集可能上百年后会对人类有用的植物种子。
· 03 ·
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钟扬在收集珍稀物种的同时,也强烈意识到,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物学家,更需要的是教育工作者,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学生心中,泽被后世,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。

钟扬在西藏大学上课
援藏16年,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精心培养下,一批藏族科研人才脱颖而出,钟扬身兼复旦大学、西藏大学两校博士生导师,最引以为自豪的是,培养出了藏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和哈萨克族第一位植物学博士。

201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,藏族学生给钟扬献哈达
“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,探索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支教模式,帮助西藏形成人才培养的造血机制。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,但我的学生们还在,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。”
在他的学生眼里,他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,但他在课堂上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的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,足以感染到每个聆听过他讲课的人。
毫无架子,爱生如子。所有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,一半以上的男同学在他的宿舍里借宿过。

钟扬为学生做饭
在藏大期间,学生们忘不了,多少个野外考察的清晨,钟老师冻得嘴唇发紫、忍着身体不适,为大家生火做饭。有些他感兴趣但是高风险的课题都是自己在做,怕耽误学生毕业。
痛风发作时,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,他拄着拐杖坚持带学生采样,而不让学生独自冒险上山。
钟扬去世后,他的很多学生都表达了对恩师无限的敬仰和怀念之情:
“这些年承蒙钟老师指导,我的第一篇论文,我的出国推荐信,钟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;8年前在异国他乡,几瓶啤酒一盘花生,钟老师和几个年轻人彻夜畅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......”
“钟老师是复旦生科院为数不多的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植物大家,专注植物保护,不与污水同流。其学识和师德均让人高山仰止。”
“上周钟老师还在微信群里招募小伙伴在‘十一’进藏考察,当时我许愿一定要在毕业之前抽个假期跟他去西藏收集种子。十月的羊湖秋水湛蓝,在湖畔找种子的那个人却再也回不去了......”
2017年,复旦大学现代生物科学导论课期末考试试卷中,命题者出了这样一道题:“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,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,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著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。”

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植物
阅卷老师发现,每个学生的答案都写得满满的,学生们对钟扬老师的怀念感恩之情跃然纸上,读着读着就忍不住让人泪流满面。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就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“教育”本质的阐释: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
· 04 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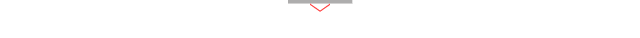
搞植物研究注定是一场孤独的“逆旅”。与位高权重绝缘,也不会令自己身家丰厚,投身其中,凭的就是满腔热血。
钟扬的学生拉琼曾到过他上海的家,“真是令我特别心寒,他的那个房子,包括房间里面的设施,还停留在1970年代的水平,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,又是在上海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,不是说钟教师没钱,但他的钱都没有花在自己的身上。”
上世纪90年代,钟扬夫妇赴美国访问,回国时却把省吃俭用积下的生活费买了计算机捐给单位。

钟扬与妻子
西藏采样多年,随身之物除了方便食品、药盒、裂嘴的登山鞋,就是几条从地摊上买的牛仔裤。
他的学生拉琼在老师的宿舍里,看到一条钟扬花29元在地摊上买的牛仔裤,裤裆处密密麻麻缝满了补丁。
一项项的科研计划,一拨拨的学子,一块块的补丁,甚至一次次的生命危险,成为钟扬短暂一生的独有“徽记”。
不知多少次进出青藏高原,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大的工作强度,使曾经身体素质很好的钟扬变得心脏肥大、血管脆弱,每分钟心跳次数只有44下。
他的妻子张晓艳说,2015年,钟扬得了一次脑溢血,后来凭着强大的毅力恢复了健康,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,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,可他不仅没有放慢,反而还‘变本加厉’。”

2015年突发脑溢血,病床上的钟扬教授
在被救治苏醒后的ICU病床上,他曾口述写下过一封信:
“这十多年来,既有跋山涉水、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,也有人才育成、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;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,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……”
钟扬作为复旦生科院研究生院院长,博士生导师,去西藏前,本可以“养尊处优”,坐享一切人生的“红利”了。但他却将16年的大好时光,将自己,交给了那片他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热土。
2002年,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出生。
孩子出生时,钟扬正在研究红树植物,遂用植物为儿子取名:云杉、云实。一个是裸子植物,一个是被子植物。

钟扬和家人合影
“到了孩子那一辈,一看名字就像找到了组织,就能聚在一起说说这个的爹,那个的娘,该有多好!”
从一缕清香找到一朵花,从一只飞鸟找到一片蓝天,从一颗植物找到一个生命,这样的追索更像是一场薪火相传的交接。
在西藏工作16年,钟扬对西藏的热爱已经深及骨髓。他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,学习藏语,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。”
他曾向妻子承诺“孩子15岁之后我带!”,却在双胞胎儿子15岁生日后的第16天倒在了讲学的途中......
“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,周末愉快!”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。

钟扬与少数民族学生在一起
儿子在和母亲去往银川“接父亲”回家的路上,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当他们终于从媒体得知父亲罹难的消息后,在QQ空间悄悄写下:父亲,我们还没有长大,你怎么敢走!
云杉,云实,是他生前爱的寄望,在他离开之后,成为他在另一个世界永远的守望......
· 05 ·
一千年前,抱病之中的诗人陆游写道:位卑未敢忘忧国,事定犹须待阖棺。
钟扬总是有那种“时不我待,只争朝夕”的紧迫感,而这种紧迫感,是源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:哪怕是多收集一个物种,多培养一个学生,多栽下一片树林。
生前,钟扬想为上海造一片红树林。但从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讲,红树林分布在低纬地带,学界普遍认为上海不可能成活。

钟扬在上海临港地区试种红树林
钟扬偏不信邪,希望破解红树北移难题,探索50年后在上海见到最美海岸线的可能性。
他带回了10种红树林幼苗。第一年由于冰冻灾害让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,钟扬没有放弃,对各种树种进行耐寒筛选。第二、第三年奇迹发生,幼苗存活,他说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,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”。
30余年从教、16年援藏、10年引种红树,他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祖国的植物基因库,在青藏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,收集了1000多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。

为小学生做科普
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,他在无数人心中播下的信仰的种子:无论是沃土千里的平原,还是滴水成冰的极寒地区;无论是莘莘学子的人生蓝图里,还是无数心存愿景的人的期待中,这些被撒下的科学的种子,也是人类未来的种子。
他延续的是,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 复旦学生悼念钟扬教授
复旦学生悼念钟扬教授
在浮躁喧嚣的当今社会,他以自己的奉献和坚守告诉了我们,什么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“流量”和责任担当。所以,钟扬教授的演讲今天听来,仍令人振聋发聩:
“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惧。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。而我们采集的种子,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。到那时,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。”
四月,草长莺飞,大地葳蕤,那个采种子的人却一去不回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