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辛上邪
躲过了黑夜的那只鸟
最后还是消失在黑夜里
01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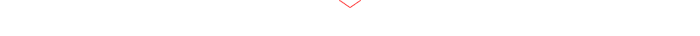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80岁的坎温老人靠墙坐着。消瘦的身躯和四肢满是劲道。他不说话,眼睛盯着手里的活儿,手不停地忙碌着。他在做伞,傣族的油纸伞。30个小竹片削光滑,作为支撑的伞头上凭着感觉锯开开口,也是30个,外面的大伞骨还要削30根竹签。竹签里外一层层次第埋下、串线,再巧妙地用线把伞骨绷成圆弧状,就成了伞骨。



也许是先前串的太紧,最后这一绷,坎温老人绷了八次。滑脱一次,重来一次。重来一次,滑脱一次。一直到第八次才成功。

所有这些都是凭几十年的感觉。几年前,傣族油纸伞被媒体报导时,村子里还有四位老人会做伞。如今,只有坎温老人一位了。无论是否有人买,坎温每天都这样靠墙坐着,默默地做着他的伞。他的妻子,79岁的温扁是他的助手。

一把伞要经过几十道工序,材料就是竹子、纸张、棉线;插入一根竹条,就能做成弹簧;涂上菜籽油便可防水;抹上锅底灰和特别的植物制成的颜料,伞面变得古朴动人。

寂寥的雨巷中,伴着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彷徨而去的不知是否是这款油纸伞;凤尾竹林中的傣族妹子必曾撑着它遮阳躲雨。傣族油纸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然而会做的人已风烛残年。

02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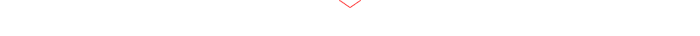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坎温和他的油纸伞是五集纪录片《寻找手艺》中所记录的众多的匠人和他们濒于消失的手艺之一。
《寻找手艺》是导演张景卖了房子加上友人赞助,自费和他的两三个非专业伙伴花了129天拍摄、又花了一年多剪辑而成的。他们开着一辆旧车,行程34300公里,跨越23个省,拍摄了88个区域、144个拍摄点,记录199名主要手艺人。之后,剪辑制作了近60次才定稿。
摄影是张景和司机临时转行担任,录音师也是出发前临时自学的,片子拍得相当“不专业”,拍摄中匠人们都在实打实地做自己的活儿,没有摆拍。就是这份“不专业”,片子被多个电视台拒播。

2017年1月,在27院进行首发仪式。有位小观众留言说,寒假中,他看了六遍,能把台词背出来了。2017年4月19日,B站首次上传。点击率迅速飙升,形成一次次观影小高潮。如今已经是B站综合类排行第三,被观看20万次,弹幕逾两万条。
这是张景第二次穿越中国,上一次是他在大学期间骑自行车的穿越。从小生长在农村,工作后又跑遍全国拍片,张景见证了手工艺的多彩,也见证了它们的日渐衰落。在不惑之年,他下决心去用影像记录尚有余温的手工艺,让人们知道,“中国,远远不止你身边经常看到的那些现代文明”。

03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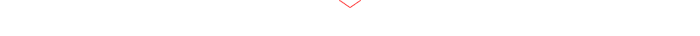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在喀什,只有吾麦尔艾里兄弟和他们的叔叔吐尔逊江.祖农还在制作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吾尔族土陶。炉窑设在家中,作坊隔壁是起居室。烧窑的时候,吐尔逊江.祖农不能离开半步,他要凭着眼睛和经验来判断炉火的温度。

开发商要征地,给他12套单元房他不要。吐尔逊江.祖农说他家的房子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祖辈留下的房子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,他拍拍自己的脸,那意思是说“我是要脸的”。祖辈的手艺也不能在自己手里毁了。不在乎赚钱多少,他只是要多做,宁愿售价低卖得多,这样能给世人留下更多的陶器。

戈壁荒滩上,张景他们找到了胡达拜尔地。这位老人会制作、演奏巴拉曼、热尔普、都塔尔等民族乐器。他只是个放羊的老羊倌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他的音乐撼动人心,“向北90公里无人,向南8公里无人,向西11公里无人,唢呐的声音以胡大拜尔地为中心,抚平整个戈壁滩。”


老人的牙齿已经松动,吃囊要捣碎了吃,再加上杯白水就是早饭。为了款待几位拍摄者,他把家里的鸡蛋煮了一半。拍摄者们走后,他的生活还会继续。继续牧羊、继续在沙漠里种玉米、继续做他的芦笛。他的音乐恐或后继无人——连他儿子都没有跟着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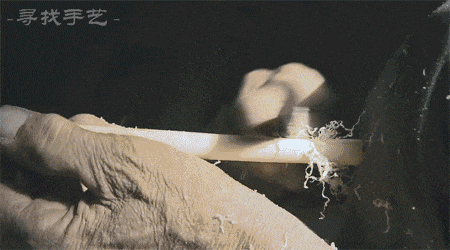

04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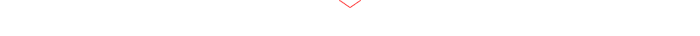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西藏麦宿是个神奇的所在。两万多居民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杀生,没有人外出打工。他们都留在乡间做各种自己擅长的手艺。很多是大师级的,铸铜大师尼玛、唐卡大师次平的作品预定期都在四年以上,编织大师扎西巴姆还有自己的品牌“子乌”。香港演员吴镇宇刚买了一只子乌牌子的牦牛毛编的手工包。

达瓦扎巴拿着的包就是吴镇宇买的同款包

达瓦扎巴说,他去过好几个大城市,觉得都比不上麦宿,除了出去旅游,他不会考虑离开麦宿,何况他还是铸铜手艺的传承人。他是尼玛的儿子,尼玛是洛热彭措的女婿。洛热彭措重建了宗萨寺。宗萨寺是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本寺、中国最大的萨迦派寺院。洛热彭措还是有名的藏医,他开的藏医院为穷人和喇嘛免费看病。这项花费每年就价值六七十万元。

宗萨寺成立于745年,毁于1958年。1983年,洛热彭措着手重建宗萨寺时,请不起外地的手艺人,他便派麦宿人去学。学成回来重建寺院。木工、铸铜、金银器打造、陶器、绘画、唐卡、编织等等,藏地的手艺都学了回来。也是仰仗这些手艺,麦宿人能够厮守家乡,不用出远门去做工。以他们的手艺为寺院服务,赚取家用。他们勤劳、节俭、爱清洁。他们的家像高原的天空一尘不染,心是那样澄明。

尼玛的家
05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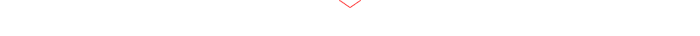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手艺人的幸福还源于不贪心。
西藏达孜的土旦次仁是藏区著名的锻铜大师,为拉萨大昭寺就打造过两尊巨型佛像。他熟悉佛教故事、典籍,不仅设计细节符合典范,还力求从佛像的体态、眼神中传达出佛像的性格。订单源源不断,但他不富有。每年,他都要为寺院捐出佛像。一座一米多高的佛像镀金后的造价就要三十多万元。没有钱的时候,就捐人工。


见到土旦之前,张景认为自己卖了房子拍纪录片很不一般。见到土旦之后,他的虚荣心碎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拍记录片还是有卖片子赚钱、做一项“工程”的名利之心。而真正做事情的态度应该是像这些手工匠人制作作品时那样,先把事情做好,其他的无需顾虑太多。土旦不为了钱而雕塑,江雍次仁也不为了钱而刻经文。

德格的印经院要重印经书,招募来几十位刻版艺人。“一年多下来他们才刻了1500块,后面还有4万块板子等着他们,按这个速度,他们还需要26年。”刻板的艺人抱着打好底稿的经版迎着光坐在窗前,一刀一刀地按照字样刻下去。不疾不徐。13岁开始刻版的江雍次仁已经刻了8年,他说:“刻的时候好好刻,不好好刻的话,我们马上马上就刻完了,慢慢刻的话,对这个板子好一点嘛。”他说,不好好刻,死的时候会害怕,“良心过意不去”。

张景的一位同学在生意失败、家庭破裂后曾要自杀。寻死的那一刻想到了孩子。回家后,夜深人静时,他找出张景送的这套片子看了起来。看到江雍次仁这一段,“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十遍”。他甚至找张景要江雍次仁的照片,说要挂起来时刻告诫自己,“生命也可以这样”。
06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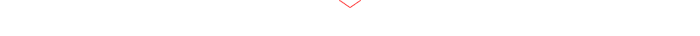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安徽万安的一座庭院中,匠人师傅们在做罗盘。罗盘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,天文、地理、军事、航海、占卜,阴阳宅看风水的必备仪器。万安是全国唯一保持传统罗盘制作技艺的地方。做罗盘的木头要用风干三年以上的上好银杏木,刻盘面、木炭一遍遍抹出格子、刮白、干草打净、再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写下盘面上的字。三千字,蝇头小楷,不能有丝毫差错。上漆、打磨。打磨要二十多遍,一天一遍。最后由师傅上针。上针是保密的,不许外人观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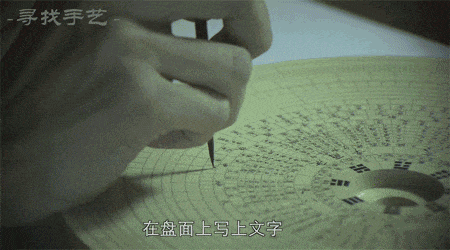
泾县小岭村。这里有上千年造宣纸的传统。青檀树皮煮熟,以前用石灰、现在用碱漂白,挑出杂质和不够白的树皮,打碎成浆,用竹帘捞起,挤压水分,晒纸——将湿纸一张张分离,展在烧热的壁炉上摊平烫干。晒纸一定要由一对夫妻来操作,这是老辈子留下的规矩。中国最好的书法用纸就这样造出来了。

质量好不在于配方神秘,而在于认真。捞纸的竹帘是本村匠人编的。两个人快手编,一天能编20厘米长。席子编好后,还有涂漆、刷匀、晾晒等工序。漆是土漆,是从漆树树皮上割下来的树浆。涂漆必须用丝绸揉成的团来涂。刷子是猪鬃毛做的。手工艺的精髓在于一份执着的讲究。千百年的规矩不会轻易改,每一步流程不偷工减料。

小岭村的宣纸造纸废水都直接排放到流经村子的小溪里。小溪的水仍然那么清泠。错的不在于发展生产,错的在于现代制造业没有良心。

07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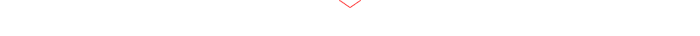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手工艺谈不上精致,它们曾经是生活的必须。手艺人做的时候想到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在用。那份将心比心、感同身受的贴心,让看起来粗糙的东西精细了,有了温暖。温暖日久弥深,代代传递。

彩云易散琉璃脆。美好的东西在这个生猛的时代禁不起摧折。
贵州小黄村的真、养号两位老姐妹打算把剩下的原料全部用完、做完此生最后一次纸时,恰巧被张景他们遇到了。一天可以做十多张纸,这样的产量竟也积压了几百张。销路不畅,岁数也大了,做不动了。做完今天这十几张,小黄村的这项造纸术便也失传了。
拍摄之后,张景给老人们拍了照片并通过显示屏让老人们看了,还记录了她们的名字。她俩高兴了,说:“这样的话,我们的照片就可以去北京了,就算名字到了北京也好呀”。播放后,这一段弹幕特别多,“阿妈,你们到北京了”,“已到广东河源”,“已到深圳”,“已到俄罗斯”,“已到纽约”……“已到温哥华”。手艺失传的落寞像水纹一样越扩越远,越散越淡。

真和养号
却并非所有的人物都被选入了正片。比如山东泗水土陶末代传人刘新文。他虽然有代表性,“几乎是中国传统手艺和手艺人的一个缩影”,但是,“太悲凉了,看到他,心里总会有一些没落的寒意”。
心生寒意的是旁观者。而更多的手艺人,“知道自己的手艺已经走到了末端,却不悲观,不抱怨,尽自己的可能,让手艺多延续些时间。”
也许,这就是工匠精神的一种。手艺人从来不问什么是工匠精神,他们连想都不会想,“他们出于生计,或出于兴趣爱好,或只是一种习惯。但他们都在默默无闻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温度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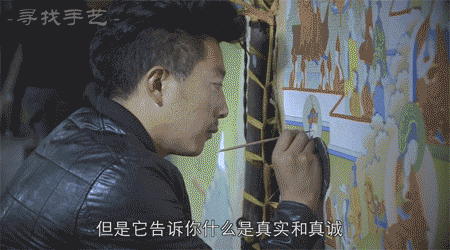
片子播出后,有二十多人联系张景想买坎昆老人的油纸伞。电话打过去,获知老人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了。再也没有人靠着墙日复一日地做一把竹伞了。
无数手工艺人渐渐凋零。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存在过,丰富了先民的生活、缔造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。也许有一天,所有的手艺终将消失,甚至连人类也不会存在。但是,他们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。和我们一样。
“森林里的一棵树,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,如果没有他们,森林将不复存在。”
森林里的一棵树
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